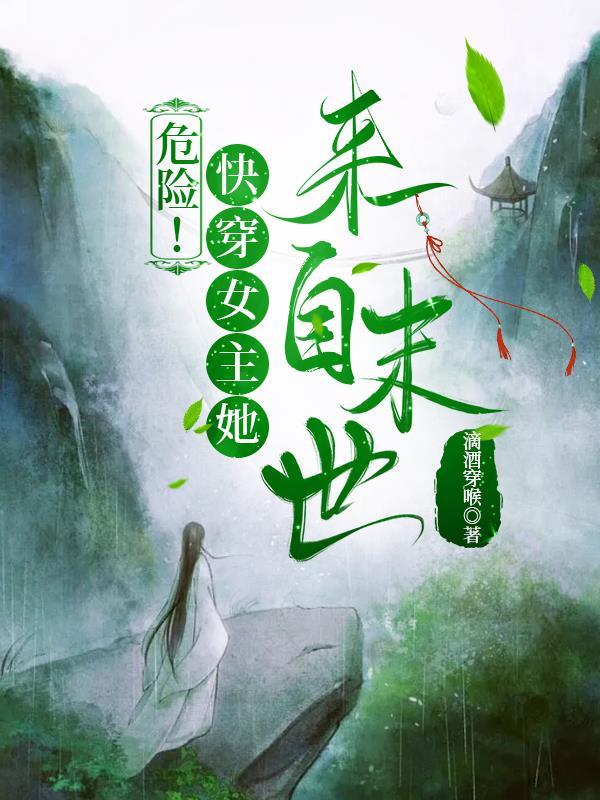500小說>抑郁質和多血質偏不穩定 > 第6頁(第1頁)
第6頁(第1頁)
好在助理姐姐想了起來:“哦,你微博接的那個,七本家的奶茶推廣。”
媽媽轉過頭看向我:“你還關注我微博了?”
百密一疏,這不就暴露我了。
我為自己捏很多把汗,幸好我媽沒有追究,隻是說:“不知道好不好喝,我拍完照就丢了。你要喝?我讓Cindy去買。”
Cindy就是助理姐姐的名字。那我怎麼好意思呢,我說不用不用,回了房間安分待好。
晚飯是一桌本幫菜,蔣阿姨很盡心,使出渾身解數,燒了八菜一湯。要知道,換到平時我三四天才能集郵般湊整出這個數量。
飯後我在客廳徘徊,很想和爸媽分享我的高中生活,包括換了個領袖型同桌,累計問我借了兩千這件事。不過媽媽洗完澡在房間裡敷面膜,爸爸在書房辦公。
我溜溜達達走了半天,沒人從房間裡出來,隻有蔣阿姨洗完了碗拿了iPad在餐桌看韓劇,我隻能回自己房間了。
沒辦法,父母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理想,我們做孩子的也得多包容理解。
快到十一點時,突然有人敲了敲我的房門。
爸爸穿着他莫蘭迪灰的絲綢睡衣走進我的卧室。
我把書本倒扣在胸上等他開口,他像每個公益廣告裡演得那樣,坐到我的床尾,關切地看向我,用低沉的聲音和藹地問:“學校還适應?真的不用出國?”
我内斂地笑了一下:“挺好的,不用出國。”
爸爸可能覺得,依靠自己的财力,能給我提供更好的教育資源。但我已提過,我是個脆弱得堪比室内盆栽的人,對新環境的适應能力很差。
如果讓我出國,我會為一些普通的生活場景憂愁。比如一個人去陌生的大超市把所有日用品都買全,還得結賬、等車、拎着大包小包回家;比如如果晚上水管爆了要怎麼辦,是要大半夜崩潰地找維修電話嗎?又比如在全是各色人種,熙熙攘攘的食堂,要一個人對着窗口說我要這個這個這個,我會覺得很有壓力。畢竟我是一個連網紅奶茶店都不敢一個人打卡的人。
這些在普通人看來瑣碎的事情,件件都能是我心中的大山。
爸爸被第二次拒絕,也沒生氣,隻是點點頭讓我早點睡就走了。
第二天,也就是國慶節當日,爸爸帶着媽媽和我去了黃浦江畔。
窗外是白天的江水和遊人,包間裡我局促地坐在位子上,而服務員正半跪着給我剪蟹腿和蟹鉗。紅澄澄的蟹被肢解成蟹殼,軀幹和腿,蟹殼翻着朝上,露出油汪汪的蟹黃。蟹鉗被剪開,裡面是富有紋理的白色蟹肉,我已經聞到香味。
爸爸看我不動,邊吃邊說:“筱筱,吃啊。”
我點點頭。可是旁邊那個半跪着盤着發穿着旗袍的女孩,還帶着口罩在替我剝殼卸腿。我有些坐立難安,我何以配得上這種服務,為什麼要發明這種服務啊。
好在爸爸和媽媽開始聊天,我微微側過頭,對把最後一個蟹腿放在我盤子裡的姐姐說:“謝謝。”
她口罩上的那雙眼睛睫毛很卷翹,眉眼彎了彎,說:“您慢用。”
我想她對我的客氣可能也是工作需要,我有一些愧疚。
吃完飯,爸爸又帶着我倆去了江邊,一輛遊艇在等我們。我又頂着衆目睽睽的眼光登上去。
我聽到身後有人問門票在哪裡買,安保人員禮貌地說這艘船是私人使用的,我便又聽到很響的一聲啧。
江邊的建築逐漸遠去,偶有落地平台上的遊人在朝這裡看。我的耳朵還有點發燙,裝作若無其事,突然想到自己曾經也是注視的一員。
在我馬上就要讀小學的夏天——當時我還和爸媽住在大院的一樓。一個普通的星期六,爸爸把我和媽媽帶到了正大廣場。我不敢踩上扶手電梯,是被媽媽抱上去的。我們在樓上的必勝客吃了我人生第一頓西餐,餐廳的落地窗對着黃浦江畔,空調開得很涼,我坐在爸媽的對面蕩着腿看玻璃外明麗的天空,聽到媽媽點單時小聲說:“好貴啊。”感覺藍天比江水離我更近。
飯後爸爸帶着我和媽媽在商場裡逛了一圈,爸爸買了件襯衫,媽媽買了一條粉紅色的連衣裙。等到夜晚氣溫降低,我們又去了外面的濱江大道。我永遠記得那個時刻。
爸爸摟着媽媽,指着粼粼江水對面華燈初上的建築群:“總有一天那裡有我的位置。”媽媽幸福地依偎在爸爸懷裡,什麼也沒說,隻是很深地點了點頭。
當時的我仰望着他們若鴛鴦交頸的背影,覺得自己很渺小,心想怎麼不帶我一個呀?于是我費力抱住媽媽的腰胯,任憑夏末的晚風吹拂在臉上。
帶着記憶的風撲面而來,此後我們三人聚少離多,起初是我和媽媽等爸爸,然後是我等爸爸媽媽。後來也不再講等待一說,因為即使過年時也常常隻有媽媽會在家,分離才是常态。
請勿開啟浏覽器閱讀模式,否則将導緻章節内容缺失及無法閱讀下一章。
相鄰推薦:荒涼地 喜遇良辰+番外 口欲期 我們強O不逼A的 假少爺淚失禁後成了萬人迷 夏天+番外 在天災魔女成型前,将她們攻略 玫瑰花房+番外 無何有鄉+番外 (僞裝者同人)鳏夫獨白+番外 時空流界 人間相逢 季節性戀流感 不要亂摸石頭 我的養狗方式好像有問題 經濟與法+番外 我與病嬌共沉淪 驚!清貧校草是孩子他爸+番外 我怎麼可能有五個爸爸[星際] 請君問夢